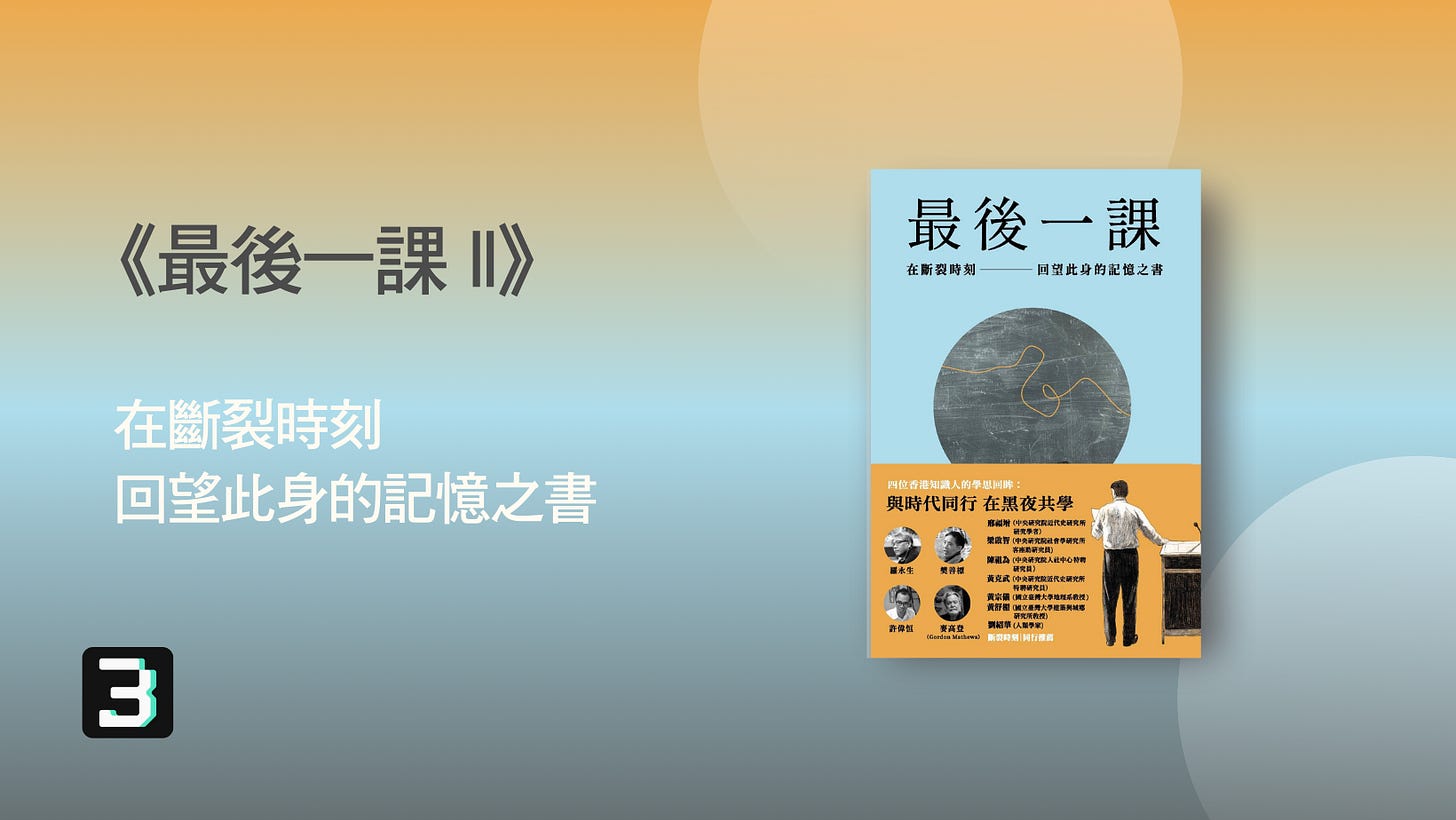身份認同的多元想像 ─ 讀《最後一課 II》
從社會學、文學、歷史及人類學的角度出發,關懷的主題卻不約而同。
飛地出版了新一本《最後一課 II》,由羅永生、樊善標、許偉恒和麥高登四位老師執筆。他們的共通點是:都曾從事教育工作,都已離職,都有非常的熱忱。四篇分享像是他們對自己的教學事業、甚至人生階段的小結。
若要把最珍視的學科知識及人生價值,煶煉成一堂課作為餞別的禮物,幾位老師會說什麼呢?
第一次接觸「最後一課」這題目是在中學的中文課本,一篇由法國小說家都德所撰的同名短篇小說,我想出版社為此書取名《最後一課》,多少是想關聯該小說的意念。故事講述普法戰爭後,法國一所村校中老師跟學生上的最後一堂法文課。小說表達出濃烈的國族情感:最後老師因不能再教授本國語言而懊悔,最後在黑板上寫下「法蘭西萬歲」幾個字。但《最後一課 II》的內容卻遠超狹義的國族情緒,跟小說共通的情節只是老師因各種原因告別跟學生相處的學校,並利用最後一課的機會講授自己最珍視的知識。
有趣的是,四位的分享雖從社會學、文學、歷史及人類學等角度出發,卻不約而同地提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議題。尤其那些幾乎是自傳式的故事,娓娓道出他們成長與價值觀模索的經歷,莫不跟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滄桑相關,帶領同學思考身處這時代的「香港人」可以怎樣走下去。
我們無法不承認香港目前的崩壞狀態,但除了婉惜和悔恨,更需要思考如何建立新的主體個性,走出自己的路來。學校本應肩負此使命,而非倒模般生產「愛國者」或標準化的齒輪;那種專制的管控手段,稱不上教育。然而,所謂「走出自己的路」,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路?這可沒有簡單便捷的答案。
群體的主體性
羅永生教授批判近年香港的「反殖」運動,認為那是國族主義者在掛羊頭賣狗肉,口說反帝反殖,實際卻繼承甚至加強過往殖民者的惡政。他點名狠批某些「學者」借社會學專業推動反殖運動,只是為了左右逢源加官晉爵,無助香港人真正脫離殖民者而自立。
文章令我最深刻的,是他如此寄語立志服務社會的「知識人」:
香港的知識人不單要有勇氣向權勢說不,更要讓自己不要迷失在眾帝國互相進行認知作戰的漩渦中間,要認真尊重歷史,坦誠面對在「帝國之間」所塑造出來的、複雜的「自我構成」。在與民眾同行推動抵抗的運動中,貼近民眾的生活和苦惱,不斷反思實踐的經驗,發揮批判思考的功能,區分只流於亢奮的民粹主義,與逃避責任的犬儒主義。能如此去為自己的知識工作定位,那不管你是拿起筆桿,或是舉起鏡頭,不管你是透過影音去影響輿論,還是埋頭為新書寫作,你都會知道如何才能「活得磊落真誠」,如何才能真的以「知識人」作為你的「志業」。
記得幾十年前還在讀中學時的某次早會,當大家都在炎熱的天氣中汗流浹背地站在雨天操場,無奈地聽著老師演講之際,我竟記住了講辭中提及的那段對聯,念念不忘直至現在: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可是現在我的生活中,已鮮再有人提及「讀書為何」這話題了,就算工作上遇到志同道合者,也是靠默契協作,不再提「志業」二字。可能因此,今天讀到羅教授的這段文字時,竟不免感觸。
回應躁動時代的知識
若說羅永生老師的課比較直白,那麼樊善標老師的課則比較婉轉。樊善標老師於 2019 年 8 月被邀到中文系迎新營演講,題為「躁動時代中文人」 ─ 那年,我親眼看見百萬大道上,從大學圖書館的風火台一路到理學院的「飯煲底」,擠滿黑壓壓、躁動的人群 ─ 他如此總結演說:
知識實踐的兩個方面,一是透過學習知識而選擇立身之道,把知識化為行動;二是由學習知識而體會世界的多元與複雜,對人和事多一點理解包容。
這句話可說是他這最後一課的主旨,一方面求學者不應自我封鎖於象牙塔內,要學以致用;另一方面愈求知愈要謙卑,應知達至善者不止一途,個人和家國的關係錯綜複雜。這是他作為文學人回應躁動社會的取態。
文學是文字運用與想像力的訓練,要對抗的是拘束失語、思想狹隘,而這狀態卻是在躁動的社會中最常見的,我自然也無法幸免。以上那句話是老師給我的最大提醒。
帶出同理心的歷史
許偉恒老師因有感無法在現今香港的環境誠實地作一個稱職的老師而放下教鞭,我能從他的文字中看出他對歷史真相的執著,並且薪火相傳的志向。他提及陳寅恪和余英時兩位前輩的故事對他的啟發,反複勸勉同學擇善固執,不能妥協接受被扭曲的事實。我想,在國家機器龐大的敍事力量面前,也多得如他一般的許多同仁的努力,後世對世界的認知才不致於完全被謊言淹沒。
此課給我最大的提醒,卻是老師論及研讀歷史能助人產生「同理心」,因為每件歷史事件的發生,每個人當刻的行動選擇,都必須配合前後的歷史脈絡才能真正被理解。這道理雖不難懂,卻經常被忽略,甚至有心人會刻意抽空歷史脈絡以曲解事件以達至其目的。
同樣是歷史專科的邢福增教授在他的「最後一課」中也曾說:
歷史不僅只是瞭解過去發生的事情,理解過去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認識現在。我們總是帶著現在的問題,當下的困惑,進入歷史的世界,目的就是要梳理出一條路是怎樣走過來的脈絡與線索。
香港史自英治時期已然不受教育系統重視,現在更滲進了愛國主義的敍事。香港人若想建立主體性,須竭力保存真實的、沒被扭曲的歷史,並且認真研讀,所走的方向才有堅固的根據。
多元的人生可能
麥高登教授的課,回望了他精彩傳奇的一生,非常有趣。他跟以上三位老師不一樣,不是香港本生土長的華人,本籍美國,伴侶是日本人,二人卻已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年,且很喜歡這城市。他的專科是人類學,研究的課題十分多元又有趣。可能因為以上的背景,他看「香港人」的定位有更宏觀和獨特的角度。他在文章一開首便提出自己最關心的問題:「人活著的理由是什麼」。他參與社會行動主要基於愛,多於對公義的執著。
讀畢他這一課後,我像從狹隘的「香港人」身份定義中短暫抽離出來,看見人生更多的可能。
他認為香港是個多元的集體,並觀察到在反送中運動後,香港人對其他族裔態度的微妙變化:對世界各地不同種族的族群多了包容,除了中國大陸的「同胞」。這事令他難過:
香港認同的基礎,已經從族裔身份轉變成了某種公民身份,正如那位本土行動者堅持的,任何人都能成為香港人,但大陸人除外,這與香港政府不斷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位行動者的態度固然帶有種族主義 —— 任何群體都不該受歧視,普通人也不等同於他們的政府 —— 但這種態度卻很耐人尋味,它彰顯出年輕一代對香港身份認同的感知可能正在發生變化。
回顧香港的歷史,人口的構成本就有大部份是來自包括中國大陸的移民。教授所觀察到的這種排他情緒,實是源於強加於大眾的價值觀及政策的反彈。說到底,身份認同可能不是一件能以教育硬性設定的事。若硬要去設定框架,反而會適得其反。這原則適用於政權以行政手段強加於大眾的身份,當然也適用於群體以至個人之間相互標籤的身份。
未完的課
雖然四位老師都已離開教職,慶幸我仍能藉文字學習他們的教誨。閱讀就是有這樣的功用,讓教與學突破時空限制,就如許偉恒老師受陳寅恪和余英時兩位前輩的啟發一樣,上下四方、今來古往。希望大家都能藉閱讀有所禆益。